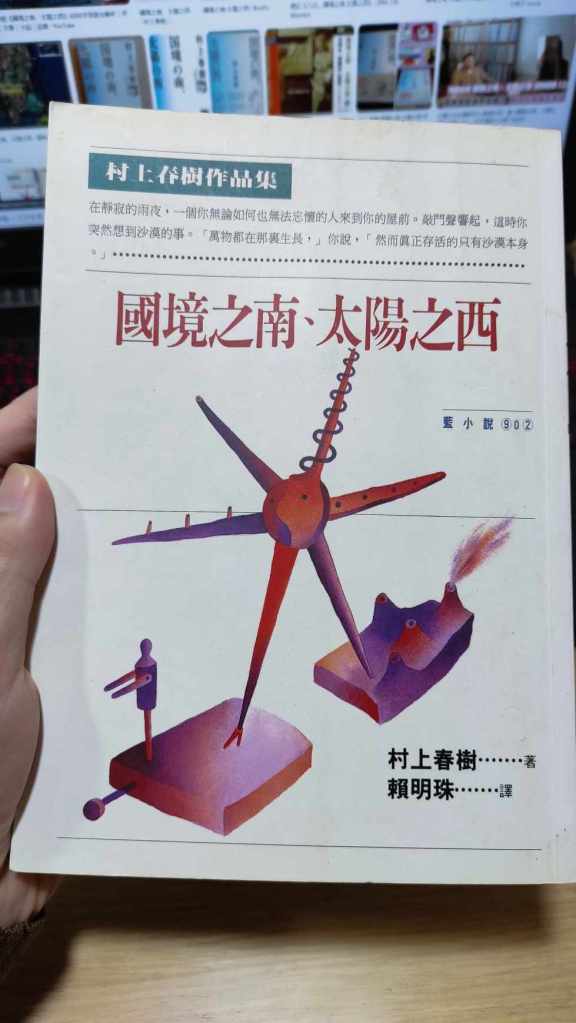
音樂家-David Gilmour 人的一生未必只有一次真愛,但以某種方式、某種絕對的心情(墜入情網),確實只有一次。
一切從格格不入感開始
故事從男主角(阿始)出生在一個經濟條件優渥的住宅區開始,在那個地段中,獨棟的住屋是相當常見的,而身為其中的一份子,主角經常感覺到一種格格不入的感覺,或可以說是對生活的割裂感。
村上春樹在小說中很細緻地去描繪這種感覺,用了大量的段落、不同的比喻方式,像是「最後只剩下沙漠存在」、「真空的窒息感」、「沒有中間性的東西」及「西伯利亞歇斯底里症」的比喻,都是這本小說之中不斷反覆被描繪而出的存在性徵,也可以說是男主角一生中的基調。
如同在《人間失格》中,主角阿葉那份在人群中如小丑般格格如入的感受類似。也讓我想到哲學家齊克果(Søren Aabye Kierkegaard)在他的日記中,那深深的憂慮與悲觀。他對世俗的不耐與厭惡,以及在人群中俗套卻又逃脫不了的「閒聊」中,完全可以從他對派對活動的經驗書寫中可以體現而出。
「我剛從一場派對回來,我是派對上的活力與靈魂:我字字珠璣,人人都因此歡笑,崇敬我—但我走開,我在這篇日記裏確實需要用到如地球軌道一般長的破折號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我想一槍斃了自己。」
《齊克果日記》,1836年。
唯一不同的是,這種對生活的格格不入,在齊克果晚年時期,最終是透過宗教的寄託而得到釋放。而阿葉以及阿始這兩位男主角,他們的一生都在找,透過愛情、透過性交,透過不斷更換的女人,向外找尋著什麼,用來填補那個在體內空蕩蕩的位置。
在小說中,阿始的這份格格不入感可能是來自於他身為獨子的身份,從小他就聽盡了對於獨子的負面標籤:被父母寵壞、虛弱的、任性得可怕。獨子意味著好像缺少著什麼的一樣,而他自己雖不願意承認,卻也不得不承認自己就是那樣被父母寵壞、虛弱的、任性得可怕的那種人。
帶著這種命定的缺陷,阿始在12歲遇到了他的真愛,而且正如我開頭引用David Gilmour的話,那種一生中只有一次以絕對心情落入的那種真愛—島本。
這位同樣也是獨子的女主角,有著許多與阿始共同的興趣,且她自幼就不便於行的左腿,對主角來說更印證了這種好像缺少著什麼的缺陷,在地上劃出了優美的弧度,並且沈溺於這種步伐而開展出的時間性,且女主角堅強而收斂的個性,那瞳孔深處的靈魂,使阿始每次想到便無法平靜。對生活中充滿著格格不入感的阿始來說,女主角的出現好似撫慰了阿始內心飢渴的靈魂。
這種感受可能就像動物本能的銘印效應(imprinting)一樣,阿始嵌入了只有這個女孩能夠填補我內心的想法,而且執著得令人可怕。不便於行的腿、喜歡爵士與古典樂,這些女主角的特徵,成了他日後尋找島本的蛛絲馬跡。
正如某次朋友介紹一場相親聯誼會,男主角聽見對象是一位腿腳不便的女子,原先興趣缺缺的他一反常態,執著地想要立即跟她見面。又如在路上看到一名不便於行的女子,阿始懷疑是否是島本本人,而跟蹤了數小時之久,最終沒有勇氣開口確認,使他悔恨了許久。
可以說,對自身命定的缺陷感,搭配上命中注定的愛情,使得主角深深地相信了非這個女人不可的癡戀感情。縱使在未來他已經成為了事業有成、家庭和睦的人,在東京青山街區擁有一處四房兩廳的住屋,還有一棟在箱根的渡假別墅,以及兩名可愛的女兒。
正如主角說:「我是愛她們,非常愛,而且非常珍惜,正如妳所說的。我有家庭,有工作。我對兩方面都沒有不滿,到目前為止,我想兩方面都很順利,我想甚至也可以說我很幸福...」當他再次遇到島本時,他靈魂深處那個缺陷的自己重新冒出了頭,甚至渴望能不顧一切地拋掉所有擁有的東西,在那一夜的幽會中跟著島本遠走高飛。
對存有意義的不斷提問
小說看到一半,或許讀者會想要反問,像阿始這樣的人生到底缺乏了什麼?小說中描述的那種割裂感與孤獨感到底是什麼,讓阿始這樣的人渴望著不顧所有地拋棄掉一切?簡單來說,他到底在「不滿足」什麼?
爬梳主角的生活處境,他從學校的經驗中常感覺到來自同儕對自己的不了解,彷彿獨子就是異類一樣。他亟欲離開那個環境,使得高中搬家後就與青梅竹馬島本分離了。又鑑於自己不知道島本是否願意與自己見面,怕造成他人的困擾,不再與其聯絡,這使得他錯失了第一個轉捩點。
反倒是高中時期認識另一個女孩—泉,雖然個性與嗜好與自己大為不同,與島本比較起來話題仍不夠有內涵與深度,但仍是一位無可挑剃的好女孩。
但主角卻因為「在泉的身上,並沒有那個為我存在的東西」的想法當中,用行動深深地傷害了泉往後的人生。正如主角說:
那時候的我卻不知道,自己可能會在什麼時候,對什麼人,造成不可挽回的深深傷害。人類在某些情況是:只要這個人存在,就足以對某人造成傷害。
《國境之南、太陽之西》,頁34。
高中結束前與泉分手後,阿始過上了十多年的孤獨人生,乏味的出版社工作,但不得不繼續下去的生活。在28歲還單身時,主角迎來了第二個人生重要的轉捩點。
他在街上遇到一個與島本動作相仿的人物徑直走過街區,但他依然像第一次一樣,無法為自己做出任何有意義的決定,只能默默跟蹤對方數小時,直到對方驚恐地搭上計程車離開。在後來,主角才終於知道這個人正是島本,但為時已晚,彼此的身份已不像28歲那時,身份單純且無後顧之憂了。
主角直到30歲的一次與未來妻子—有紀子的邂逅,才終於訂下了終生。主角的岳父是名有手腕有相人能力的企業家,他大力地幫助了主角一家的生活。而正是這樣的順水推舟,又使得主角再次陷入了深深的煩躁感。「那彷彿不是自己的人生,好像誰都可以代替我,獲得這樣的幸運生活。」
37歲時,在阿始再次遇到島本之後,他原先看似已經步入平穩的人生再次亂了套。且對於島本常以「暫時」、「可能」與「中間性的東西並不存在」這些不確定性的詞彙,來形容他們下一次的相會,更使得阿始常感覺自己懸浮在與生活相隔一段距離的空間中。無盡頭的飄渺感,雖然主角已強裝鎮定並努力拉住韁繩,但仍被有紀子發現,並默默選擇以不戳破的方式繼續陪伴與支持他。
故事的最後,主角再次遇到泉,那位高中時期被他傷得體無完膚的泉,他看著那眼神空洞、已經不再有生氣的泉後,幾乎把「自己」給嘔了出來。「覺得自己全身正發出令人厭惡的氣味...我無法把所謂自己這個東西拿回來,我只是個軀殼而已,響著空虛的聲音。」當自己不存在時,這副皮囊到底裝著些什麼,而那個自己又是由什麼東西組成的?他無法回答。
同樣地,主角也無法立即回答有紀子要不要離婚,他總是不斷地悶頭想,但無法對自己的人生做出決斷。甚至在小說的結尾處,主角仍在想著那片沒人知道的汪洋上,靜靜下的那場雨。或許,他正暗自提問著:「在無人到達的地方下的雨,那雨到底算是存在,還算是不存在?若是存在,又有誰同我一樣知道那場雨的存在?」
就像王陽明開創的陽明心學,其提出「心外無物」的觀點一般。
先生游南鎮,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:「天下無心,外之物:如此花樹,在深山中自開自落,於我心亦何相關?」先生曰:「你未看此花時,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:你來看此花時,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: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。」
王陽明《傳習錄》。
深山山野間的那片花樹,自開自落,若未與我有所關連,其自開自落皆與我無關。但若映入眼簾,花的總總意象便盈滿了意識,我深知其存在,且它們不再是方才那些置身事外的存在物。它們的存在一下就活現在我的意識之海中。
爬梳完主角從年輕到中年不斷描繪的那些感受,那種飄渺感、那種不確定性,甚至是想著的那片不知是否存在的雨。這些對於自己到底是什麼的提問,就像是在對存有本身提問一樣。
我們可以說,主角總是在向外探索那些可以與自己連結的關係,可以讓自己存在賦予意義的他人,若沒有這些,他便感覺到內心無比的孤獨與空虛。他最後想著的那片雨,內心也期望能有另一個人能夠了解那片雨的存在。主角曾喪氣地表達過這樣的話,更證明了他這種悲觀且無力的性格:
「我只不過是個不完整的人,不管去到哪裡我身上還是有著同樣致命的缺陷,那缺陷帶給我激烈的飢餓與渴望。我一直被這飢餓和渴望所苦,或許今後還是一樣會被這所苦。在某種意義上,因為那缺陷本身就是我自己啊。...(中間略)...如果再發生一樣的事情,我很可能又會再做出一樣的事情來。我可能又會再同樣地傷害你。我什麼也無法向你保證。」
換句話說,主角終究沒有勇氣承擔他的存在,甚至渴望著別人來承擔他的存在,透過什麼來給出他存在在世的具體感覺。
或許是因為獨子的性格,使得他不願主動表達出他的情感與需要,使他不斷錯過人生的轉捩點。在小說中,高中女友泉與妻子有紀子,都曾經對主角的這個個性表達出不小的抱怨。且都因主角的這個特性而被出軌,受了很深很深的傷。
泉:「我想你一定喜歡自己一個人在腦子裡想各種事情。而且不太喜歡別人去刺探。這或許因為你是獨生子的關係,你已經習慣自己一個人去思考,去處理各種事情。只要自己知道,就行了。這常常使我很不安,覺得好像被遺棄了似的。」(頁44) 有紀子:「你確實是一個任性的、沒用的人,也確實傷害了我...(略)。我終究還是會接受你的。所以我沒有死。那不是資格、正確、不正確的問題。或許你是個沒有用的人,沒有價值的人。或許你還會再傷害我,但那也不是問題。你一定什麼也不知道,而且你什麼也不想問。...你對我什麼也沒問。」(頁232-236)
換作是島本,主角就展現出相當信任且依賴,幾乎不用語言地,就深信著對方能夠理解自己。但在這樣幾乎可說是靈魂伴侶的對象上,主角仍在過去幾個關鍵的時間點,幾乎像是沒辦法掌握自己人生般—或說沒辦法勇敢承擔自己的存在般—錯失了這份難得的緣份。
也難怪最後那幕,也是唯一一次島本與阿始做愛時,「原先冷靜而自我抑制力強的她,感情的線像是斷了似的,激烈地哭了起來,後用拳頭用力敲著我的背與肩。...如果我不緊緊抱住她,她就好像要支離崩潰了似的。」
我想,島本此時應該也像是泉與有紀子一樣,埋怨著主角為何總是不斷錯過,錯過青春、錯過單純,以及錯過那些無法再用任何代價挽回的一切。
而主角這份被動性格,其背後的價值觀其實是有跡可循的。就像小說中不斷提到對沙漠的譬喻一樣:「一個世代死掉後,下一個世代就取而代之。這是一定的道理。大家以各種不同方式活,以各種不同方式死。不過那都不重要。最後只有沙漠留下來。真正活著的只有沙漠而已。」
試想,這片無垠沙漠就是我們存在的世界本身。而在這片沙漠的維度下,每個世代的交替是迅速的,反正最後只剩沙漠存在,身在其中的我們就只是不重要的過客而已。這是主角所認為的人生悲劇性。
但主角所不能參透的,是如果把維度與視角只放在一個人身上,這個人怎麼樣的活?最後怎麼樣的死?以及中間總總的生活是怎麼度過的?他擁有多少的「可動性」或說「可能性」?這就相當重要了。
我們雖然只是這片沙漠中的過客,且幾乎沒有選擇地被拋擲在世界之中,承受著為了活著而總總操煩的苦。在這段有限的時間中,我們如何採取行動來籌劃自己總總的活—雖然伴隨著苦痛—但卻也是一個擁有總總可能性的人生。悲劇如主角,他命定了自己身為獨子的性格,框定了自己畢生充滿缺陷的人生,而透過島本,主角也自我暗示了自己只能從他人那裡才能夠獲得存在的意義。
而這樣將自己存在「置身事外」的主角,其不再為自己的存在負責的性格,使得他深深了傷害了那些過去對他好的女人們。故事最後的主角,他看似終於醒悟地表達:「我想,我必須要去習慣它,而且也許這次,我不得不為某人織出幻想。...如果要找出所謂現在的我有什麼存在的意義的話,或許我就不得不盡我的力量所及去繼續進行這項作業—可能。」
但下一秒,他又像是無法承擔責任地懦弱了起來,就像他無法向妻子保證不再傷害她般:「我想,天已經亮了,女兒不能不起來了。他們比我更強壯、更確實地需要這新的一天。我必須走到她們床前,告訴他們新的一天已經來了。那是現在,我不能不去做的事情。不過我無論無何都無法從那廚房的餐桌前站起來。好像身上所有的力氣都消失了似的。...(中間略)直到有人走過來,悄悄把手放在我的背上。」而那個人,雖然小說沒有明說,但我想正是有紀子那充滿鼓勵、充滿力量的手。到頭來,或許主角仍需要依賴他人才能勉強支撐起自己的存在。
村上春樹在這本小說中,提出了一種疾病叫做「西伯利亞歇斯底里」。透過島本的口吻,她向著主角說這個怪病是存在在無垠荒野裡工作的農夫,他們日出而做、日落而息,四季之中只有冬季才會休耕,在他們視野所及之處什麼都沒有,只有太陽是他們唯一的指標。
有一天,存在農夫體內的某個東西啪一聲斷掉然後死去了,於是農夫將鋤頭放下,逕自地往太陽之西那走去,走到無法再走,精疲力竭而亡。這就是西伯利亞歇斯底里。主角詢問那個死去的東西會是什麼,島本最後並沒有回應他,留下了一個偌大的想像空間。
我想,不管這個在體內死去的東西是有形的,或是無形的。那可能都是一種如頓悟般的轉變,這個轉變使得農夫拋棄了原先枯燥而乏味的生活,或說原先賴以維生的依靠不再是依靠。在這片特性如沙漠般的荒野中,農夫義無反顧地前往那個太陽之西的目標之處,而那正也是太陽下沉之處。
在海德格(Martin Heidegger)的哲學思想中,曾提出「向死存有((Being-towards-death)」的概念,意味著當我們在某一個契機中深知了生命的有限性後,我們即會開始承擔起自身存在的責任,並且好好地籌劃著自己的人生。
就像是有些罹患癌症末期的病人,在明確得知自己僅存的時間中,開始好好地生活一般。我們在人生的旅途中早晚也會有某個這樣的時刻,如觸電般啪的一聲,深知我們終將一死,並開始檢視我們從過去到此刻的人生,並向存有提出總總的問題,如:「我要繼續這樣過下去嗎?我還有多少可能性?還有什麼是我沒有做到的事情?」諸如此類的生命提問。
然後我們會走向兩個可能性:一、承擔著存在而好好地活。二、繼續逃避現況而沉淪地活。在海德格那,這稱為本真(authentic)/非本真狀態。但無論哪一種活著,海德格都是不予評價的,既無好壞也無對錯。
就像罹患西伯利亞歇斯底里而向著「太陽之西」前進的農夫們,他們離開了原本的生活而朝向未知之處,走到筋疲力竭而最後死在了荒野上。我們能說這樣的活會比原先規律的活還要來得好嗎?
無論如何,就像主角阿始般,他或許也在他的人生中面對了無數次存在的現身,也無數次向存在提出問題。最後選擇了某一條人生的路徑,繼續過上他的生活。而身處在這片無垠沙漠中的我們,也將會有很多機遇能夠直面存在現身,我們無法得知哪一個選擇最後確切可以得到哪一個結果。但我們必須要相信,我們並非是無垠沙漠中滄海一粟的過客。
而是我們可以把握住自己某些可能性,籌劃自己總總可能性(雖然通往未明之處),那個自己人生的真正主人。

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